孙权
(182—252)即吴大帝。三国吴国建立者。字仲谋,吴郡富春(今浙江富阳)人,父坚为长沙太守,兄策结交江淮世家,据江东六郡。东汉末,继其兄据有江东,在鲁肃、周瑜辅佐下,治理属地。建安十三年(208年)联合刘备,大败曹操于赤壁。后吴蜀争霸,于彝陵之战中大败刘备。黄龙元年(229年)即帝位于武昌(今湖北鄂城),国号吴。不久迁都建邺(南京)。曾派船队航海至夷州(今台湾)。设农官,实行屯田,发展生产。但赋役繁重,刑法严峻,人民不断起义反抗。
周瑜
(175—210)三国吴国名将。字公瑾,庐江舒县(今安徽舒城)人。世代为宦。助孙权兄策创立政权,官建威中郎将,吴中人称呼为“周郎”。后克皖,与策纳大乔、小乔。策死,与张昭同辅孙权,为前部大都督。建安十三年(208年)以左督(正指挥)与刘备联军败曹操于赤壁。后病逝。精音乐,时有“曲有误,周郎顾”语。
大乔
三国时桥公的长女。嫁孙策,称大乔(桥)。与妹小乔(桥)合称二乔。
小乔
三国时桥公的次女。嫁周瑜,称小乔(桥)。与姐大乔(桥)合称二乔。
鲁肃
(172—217)三国吴国名将。字子敬,临淮东城(今安徽定远南)人。出身世家大族。初率百余人随周瑜至江南,得孙权敬重。建安十三年(208年),曾军大举南下,他坚决主张联合刘备抗曹。任赞军校尉,助周瑜于赤壁大败曹军。瑜临危,荐其代己领兵,任奋武校尉。继续坚持与刘备的和好政策。
吕蒙
(178—219)三国吴国名将。字子明,汝南富陂(今安徽阜南)人。从孙权转战各地,任横野中郎将。后随周瑜等大破曹操于赤壁。受孙权之劝,多读史书、兵书,学识英博。鲁肃卒,代领其军,袭破关羽。旋病逝。
黄盖
三国吴国将领。字公覆,零陵泉陵(今湖南零陵北)人。初为郡吏,举孝廉。后从孙坚起兵,为别部司马。继从孙策、孙权征战。为安抚山越,曾相继任九县令长,杀不法官吏,所在平定,迁丹阳都尉。他善于驭众,爱护士卒。赤壁一战,建议火攻,并领满载薪草、灌有膏油的船只数十艘诈降,乘机因风纵火,大破曹军,以功任武陵中郎将。后为郡守,征“武陵蛮”。官至偏将军,病卒。
程普
三国吴国将领。字德谋,右北平土垠(今河北丰润东)人。初为州郡吏,从孙坚征伐,镇压黄巾军,破董卓。后助孙策经营江南,官拜荡寇中郎将,领零陵太守。策死,与张昭等共辅孙权。建安十三年(208年),与周瑜为左右督,大破曹操于赤壁(在今湖北蒲圻西北)。官至江夏太守、荡寇将军。
甘宁
三国吴国将领。字兴霸,巴郡临江(今四川忠县)人。初依附刘表,后归孙权。曾从周瑜破曹操,又从吕蒙拒关羽,以功拜西陵太守、折冲江军。后曹操进攻濡须(在今安徽),他为前都督,率兵百余夜袭曹营,使魏军大惊。建安二十年(215年),从孙权攻合肥,奋勇死战,为孙权所重。
张昭
(156—236)三国吴大臣。字子布,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初从孙权兄策,任长史、抚军中郎将。策死,与周瑜共辅孙权,赤壁战前,主降曹,为权所不满。官至辅吴将军。著作今佚。
顾雍
(168—243)三国吴国大臣。字元叹,吴郡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出身江南士族。初为合肥长。孙权领会稽太守,以他为丞,行郡守事。孙权为吴王,累迁大理奉常,领尚书令。黄武四年(225年)为丞相,平尚书事,在吴国执政达19年。选用文武将吏能随才授任,以正直见重于孙权。
诸葛瑾
(174—241)三国吴大臣。字子瑜,琅邪阳都(今山东沂南)人。诸葛亮兄。东汉末避乱江东,为孙权长史。后从征关羽,以绥南将军代吕蒙领南郡太守,驻军公安(今属湖北)。复迁左将军,封宛陵候。为孙权所重,每大事咨访。权称帝后,官至大将军。
诸葛恪
(203—253)三国吴大臣。琅邪阳都(今山东沂南)人,诸葛瑾长子。少知名,才捷善辩。嘉禾三年(234年)任抗越将军,丹阳太守。率兵攻降山越,以其民充兵。陆逊卒,迁大将军,驻武昌,代逊领荆州事。不久孙权死,辅立孙皓。专国政。他力主伐魏,建兴二年(253年),率兵20万众攻新城,以士卒伤病,不得已退兵。然为民所怨,不久被皇族孙峻所杀。
陆逊
(183—245)三国吴名将。字伯言,吴郡吴县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出身世家大族。孙权侄婿。精于谋略,曾与吕蒙定袭取关羽之计。黄武元年(222年),刘备率军数十万伐吴,锐不可挡,他领兵抗击,在兵力悬殊情况下,坚守七八月不战,待蜀军疲惫,实行火攻,取得彝陵之战的胜利。吴黄武七年(228年),破魏扬州牧曹休于石亭(今安徽怀宁、桐城间)。加拜辅国将军,领荆州牧。后佐太子孙登镇守武昌,官至丞相。
陆抗
(226—274)三国吴国名将。字幼节,吴郡吴县(今江苏苏州)人。陆逊子。年20为建武校尉,领其父众5000人。后迁立节中郎将、镇军将军等。孙皓为帝,任镇军大将军、都督西陵、信陵、夷道、乐乡、公安诸军事,驻乐乡(今湖北江陵西南)。凤凰元年(272年),击退晋将羊祜进攻,并攻杀叛将西陵督步阐。后拜大司马、荆州牧,卒于官。
巴赫金指出小说的来源是什么?
曾,一般是指曾经,过往。也可以用作姓氏。
曾字详解
〈副〉
(1) (形声。从八,从曰。本义未明。副词。用来加强语气)
(2) 过去发生过表示有过某些行为或情况 [once]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唐 白居易《忆江南》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宋 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3) 又如:曾不(不曾);几年前我曾见过他一面;我曾去过杜坪乡
(4) 已经 [already]表示动作行为已经进行。如:似曾相识
(5) 竟,竟然;尚 [go so far as to;unexpectedly;actually;still;yet]
以残年余力,曾不能毁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列子汤问》
〈形〉
(1) 通层。重叠 [overlapped]
有虞之王,烧曾薮,斩群害,以为民利。《管子轻重戊》
大厦曾架,拟于昆仑。《淮南子本经》
荡胸生曾云。杜甫《望岳》
(2) 另见 zēng
〈形〉
(1) 重。指中间隔两代的亲属关系 [relationship between great-grandchildren and great-grandparents]
自此而曾焉。清 洪亮吉《治平篇》
曾元时不分。
计高曾之时。
视高曾之时。
高曾时为一户者。
(2) 又如:曾翁(称他人的曾祖父);曾玄(曾孙和玄孙)
(3) 谦词。犹末 [I]
曾臣彪将率诸侯以讨焉。《左传》
(4) 又如:曾臣(末臣)
(5) 高举的样子 [high]
[凤皇]曾逝万仞之上。刘安《淮南子览冥》
汉语字典 解释
[zēng]
[《广韵》作滕切,平登,精。]
(1)副词。乃;竟。
(2)副词。则。表示相承。
(3)副词。岂;难道。
(4)副词。一直;从来。
(5)代词。表示疑问。相当于何、怎。
(6)重。指中间隔两代的亲属。参见曾孙、曾祖。
(7)谦词。犹末。参见曾臣。
(8)通憎。厌恶;恨。
(9)通增。增长;增加。
(10)通橧。参见曾巢。
(11)姓。春秋时有曾参。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cng]
[《广韵》昨棱切,平登,从。]
(1)副词。尝;曾经。
(2)深。参见曾2曲、曾2潭。
(3)通层。重叠。
(4)通层。高。
与曾相关的成语
似曾相识:好象曾经见过。形容见过的事物再度出现。
曾参杀人:比喻流言可畏。
曾母投杼:指曾参的母亲听到曾参杀人的传闻接连三次,便信以为真,投杼而走,谓流言可畏。
曾不惨然:竟不觉得惨痛。
得未曾有:指前所未有,今始得之。
曾无与二:独一无二,没有比得上的。
曾经沧海:曾经:经历过;沧海:大海。比喻曾经见过大世面,不把平常事物放在眼里。
曾几何时:曾:曾经;几何:若干、多少。才有多少时候。指没过多久。
中间带 曾 字的女孩名字
曾兰曾英曾芳曾杰曾辰曾妮
曾明曾祥曾荣曾芬曾华曾艳
曾凤曾强曾萍曾玲曾平曾亮
曾梅曾香曾志曾荣曾林曾菊
曾科曾文曾龙曾学曾军曾伟
曾红曾光曾玉曾范曾敏曾鹏
曾霞曾宏曾顺曾花曾叶曾变
曾宾曾平曾威曾昱曾女曾琴
曾勇曾君曾发曾慰曾芝曾杭
曾云曾萍曾瀛曾臻曾景曾华
曾国曾青曾斌曾沥曾辉曾海
曾美曾克曾风曾晟曾凯曾友
曾清曾建曾旭曾涛曾亭曾帅
曾娜曾财曾杰曾禹曾中曾福
曾涤曾生曾晖曾庆曾云曾虎
曾安曾会曾丽曾仙曾燕曾进
曾勤曾武曾雄曾雅曾涓曾舜
曾规曾麟曾镛曾墩曾莹曾讷
曾妹曾卓曾杏曾至曾朴曾松
曾硕曾康曾钱曾瑞曾仁曾宏
曾晶曾峰曾珺曾民曾二曾波
曾田曾保曾尧曾钢曾昕曾鸣
曾琦曾琳曾栩曾啸曾存曾鲁
曾钰曾骏曾苗曾珍曾灼曾真
曾义曾春曾珠曾祝曾翠曾鑫
曾宁曾谋曾峰曾望曾甫曾立
曾岱曾高曾红曾水曾锋曾刚
曾位曾章曾清曾木曾群曾河
曾诚曾金曾生曾江曾娣曾珠
曾琼曾惠曾德曾兵曾芹曾景
曾启曾辉曾斌曾蕙曾族曾良
曾元曾洋曾智曾路曾飞曾春
曾怡曾水曾录曾曾曾麟曾宝
曾渡曾蕾曾兴曾欣曾有曾贵
曾欐曾永曾寅曾一曾军曾书
曾玉曾光曾源曾弟曾毓曾欣
后面带 曾 字的女孩名字
玉曾一曾桂曾小曾春曾峰曾
凤曾淑曾秀曾金曾翠曾美曾
新曾会曾冬曾爱曾月曾晓曾
红曾慧曾志曾树曾瑞曾洪曾
庆曾文曾国曾学曾艳曾胜曾
建曾正曾永曾兆曾延曾芳曾
香曾木曾碧曾建曾绍曾贵曾
家曾传曾菊曾珍曾兴曾君曾
佩曾学曾秋曾海曾水曾守曾
善曾忠曾汉曾竹曾玉曾惠曾
仕曾景曾承曾增曾华曾焕曾
满曾德曾银曾开曾述曾光曾
福曾书曾继曾红曾而曾明曾
念曾茹曾庆曾发曾润曾淑曾
孟曾传曾仕曾志曾素曾青曾
江曾子曾企曾静曾广曾俊曾
伯曾献曾顺曾祝曾德曾又曾
沪曾童曾纪曾阴曾慰曾述曾
荫曾立曾海曾俊曾凯曾纪曾
革曾和曾可曾宽曾广曾望曾
子曾幼曾弟曾崧曾爱曾祖曾
光曾克曾喜曾季曾永曾穗曾
如曾亮曾祥曾效曾九曾世曾
国曾似曾瑜曾邵曾琪曾常曾
言曾所曾长曾高曾培曾九曾
术曾荣曾桐曾若曾十曾明曾
苏曾亚曾池曾炳曾诗曾之曾
巧曾琴曾虎曾钧曾叶曾筱曾
夕曾亦曾代曾自曾知曾化曾
凡曾英曾若曾临曾荣曾晋曾
聪曾婉曾宝曾安曾西曾白曾
杏曾晓曾帅曾飞曾赛曾保曾
先曾谊曾茂曾景曾晟曾梅曾
怀曾付曾生曾培曾改曾双曾
怡曾筑曾沫曾贤曾彩曾铭曾
义曾天曾晏曾雪曾小曾乃曾
一曾慰曾缵曾健曾法曾康曾
霞曾艳曾守曾希曾捷曾全曾
中曾文曾曾曾礼曾书曾洪曾
咨曾惠曾拉曾万曾耀曾师曾
燕曾桂曾珊曾于曾跃曾渝曾
承曾风曾兢曾幸曾振曾炫曾
智曾娅曾超曾逢曾米曾礼曾
内容提要:巴赫金接受与中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巴赫金在中国的接受首先是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专家的形象被意外地引入的;另一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的翻译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对中国的陀氏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之成为陀氏研究绕不开的问题,陀氏研究者对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采取了“延续性接受”的方式。不仅如此,巴赫金的接受以及其对中国陀氏研究的影响也对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论话语走出“别、车、杜”产生了潜在性的影响。
关键词:巴赫金 接受 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 现实主义文论话语转型
作者简介:曾军,男,1972年生于荆州,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专业方向为文艺学,现任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报》编辑。著有《人文之维――文化冲突中的人文学科与人文重建》、《中国巴赫金接受史》(博士论文)、《长江文艺》系列访谈“湖北作家访谈录”及论文若干。
通讯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622弄7号325室 邮政编码:200020
电话:021-53825031 Email: zjuncyu@163.com
一、意外的收获:巴赫金首先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专家的引入
刘康在其《对话的喧声――巴赫金的文化转型理论》中说道:“今天,人们一提到巴赫金,首先想到的也许就是他的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的理论。很多时候,巴赫金被认为是一位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专家,或是一位‘复调小说’的理论家。” 的确,对于中国人来说,巴赫金的名字最初是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紧密相联的。在中国的巴赫金接受史中,巴赫金首先是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家中渐渐脱颖而出,最后取得独立地位的。
1981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围绕着这一契机,国内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介绍研究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高潮。《苏联文学》该年推出纪念专辑,翻译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几部小说,发表了几篇国内学者对陀氏的评论,在其他报刊杂志上,也不失时机地推出了一些评介性的文章。巴赫金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登陆中国的。在这些评介文章中,有两篇涉及到了巴赫金。稍早一点的是夏仲翼发表在《苏联文学》1981年1期上的《窥探心灵奥秘的艺术(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创作散论)》,这篇文章正文中并没有出现巴赫金,但在论述陀氏窥探人的心灵的艺术远远超过西欧心理小说的成就时,夏仲翼对巴赫金所提出的“复调小说”做了最为概略的介绍:
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却总是有许多独立的、不相混淆的声音处在同等的地位各抒己见……他们甚至不受情节的约束,不为作者的思想所左右。陀氏长篇小说的这个特点就造成了有些研究家们称之为‘复音调小说’的基本特征。
同时,在对“复音调小说”作注的时候,出现了巴赫金和他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另一篇略晚的是关山在《外国文学研究》1981年第3期上发表的《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的一些情况》,文章正文中出现了“巴赫金”:
二十年代,苏联曾经出现了一股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热潮。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卢那察尔斯基。此外还有,朱可夫、托马舍夫斯基、巴赫庭、别尔契可夫。……巴赫庭著有《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一些问题》一书。
这是笔者所能查到的“巴赫金”最早出现在中国正式报刊上的情况。尽管在此之前,巴赫金以及他的著作肯定以原著的形式被引进了中国,中国学界肯定以阅读原著的方式接触到了巴赫金和他的思想, 但是,将之翻译成本国语言并让它正式出现在本国媒介上却具有极强的象征性意义――它标志着接受活动的“浮出地表”。正是在这一起点上,确立了巴赫金登陆中国的最初形象: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家的巴赫金。
巴赫金的最初引入揭示了接受史中的一个普遍性的现象:意外。所谓“意外”既指在接受初期,接受者对之还缺乏深入的了解和共识而出现的一些只有那个时期才会出现的现象,又指巴赫金日后在中国所拥有的地位以及所产生的影响超出了接受者最初的意图。第一,与其他任何作家、作品在最初翻译过程中都会遇到的情况一样,在最初译介巴赫金和他的作品时也出现了“译名混乱”现象,如“巴赫金/巴赫庭”、“复音调/复调” 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一些问题》”(从译介者参阅的材料来看,似乎两人参考的版本不太一样,夏仲翼明确注明了参考版本,是苏维埃俄罗斯出版社1979年出的第4版《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而关山则很可能参考的是巴赫金1929年出的第1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问题》。尽管如此,夏仲翼在随后翻译该书的第一章时,又将之译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诸问题》,这种译法一度流行了好几年,直到白春仁、顾亚铃1988年的三联书店版的译本才最终确立“《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为国内通行译名)。第二,巴赫金是搭乘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车进入中国的。作为最初的译介契机,是国内学界对苏联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成果的兴趣,或者进一步说是对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不同于别林斯基、高尔基等“经典判断”的新鲜见解的兴趣。关文中对弗洛伊德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杀父神话”说不吝篇幅、夏文则对巴赫金的“复音调小说”情有独衷正说明了这一点。尽管如此,第三,巴赫金及其作品、思想在当时并没有引起特别的重视。在夏文中,巴赫金还被淹没于“有些研究家们”之中,关文虽然将他与另外一些苏联大师级人物相提并论,但当巴赫金被定位为20年代的陀氏研究代表学者之一时,巴赫金并没有被认为是最有名或最独特的,或者说,在20年代得到公认的,不是巴赫金,而是卢那察尔斯基,更不用说巴赫金在60年代修订再版《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并引起更大的轰动这些情况都还未纳入译介者的视野。还有第四点,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从一开始就是作为有所保留的观点被译介的。在夏文中,一方面肯定了“小说艺术中采用类似音乐中赋格曲的复调形式大大丰富了表现现实的容量和力度”,但另一方面马上又紧接着评论道,“但这一点暂时还颇有争论,因为传统小说严谨的结构至少在形式上还更完整些。而且,十九世纪末沙俄社会末世景象里产生的这一复调形式究竟会朝哪个方面发展目前还很难预卜。” 其中的保留态度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在最初译介巴赫金时,似乎并没有想到日后巴赫金会成为独领风骚的一代理论大师并为国人所瞩目,最初的接受者的用意可能仅在于更好地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推进中国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的深化。因此,由于这种“意外”,使得中国第一批接受巴赫金的接受者无一例外都是俄苏文学研究者,很多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者。这种“意外的收获”一方面基本确立了巴赫金在中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专家的形象,另一方面也确立了中国早期巴赫金接受者的格局。而且,这种形象和格局在次年及随后的几年间得到进一步的强化。
二、复调的突显:《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的译介与中国的陀氏研究
1982年,《世界文学》第4期推出了一组文章: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夏仲翼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和小说复调结构问题》及夏仲翼翻译的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的第一章《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和评论界对它的阐述》。很显然,这一组文章是1981年纪念陀氏的一种延续,鉴于陀氏作品引起了国内读者的关注和争论,全面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接受更多国外陀氏研究的观点成为国内学界的需要。重译一向被视为“反动小说”的《地下室手记》、翻译颇有争议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以下简称《诗学》)第一章,显示了《世界文学》意欲将陀氏研究引向深入的努力。同时,这一事件还透露出这样一种信息:正是在进一步研究陀氏的过程中,巴赫金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理论引起了国内的兴趣,巴赫金及其思想的独特价值开始显示出来。
夏仲翼最大的贡献是对“复调小说”的译介。如果说一年前夏仲翼的《窥探心灵的艺术》中对复调小说的介绍还点到即止的话,那么,他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和小说复调结构问题》以及他对《诗学》第一章的翻译应该说是中国接受者与巴赫金“复调小说”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先看夏仲翼的介绍。首先,对巴赫金“复调小说”的译介是为了解决陀氏研究中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陀氏一向被视为“残酷的天才”,他的艺术成就无人敢否定,但其思想倾向则颇遭人非议。陀氏作品中主人公的思想是否代表着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思想,这一问题事关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倾向的评价。“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部作品确实可以有两种理解的方法:一种方法是把‘地下人’的全部议论连同有关的故事情节单纯理解为作者本人思想的独白,因此主人公的思想或作品的主题就成了作者本人的思想的忠实写照,是作者在切实地提倡这些思想。……照这样的理解,《地下室手记》只是一场政治论争的失败者和反面材料。”另一种方法就是巴赫金的复调理解:“联系着一种新的艺术见解,即不把主人公的思想等同于作家本人的思想,而是把它作为现实生活中实际存在的声音表现出来。……因此,他仍然是一个不等同于作家立场的独立的声音。” 将主人公的思想与作者的思想相剥离的目的正在于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者立场进行辩护。值得注意的是,夏文的介绍在此存在着一个明显的“错位现象”(在此并不是说夏读“错”了,这也不失为对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的一种“读法”,因此不能简单地称之为“误读”):就巴赫金“原意”来说,复调小说的提出“论述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因之对他的创作,仅仅是从这个角度加以考察。”巴赫金还说,“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论著,主要是研究他的作品思想方面的问题。由于这个思想性的问题一时很尖锐,这就掩盖了他的艺术视觉中那些较为深藏而又稳定的结构因素。” 正是因为如此,巴赫金讨论复调小说问题时首先是将陀氏作为艺术家而非哲学家或政论家进行的。但是夏文对巴赫金复调小说的介绍却首先是为了解决对于陀氏思想的评价问题,其次才是对于陀氏艺术特色的分析。也正是因为这一错位,使得中国的接受者往往有意识地将复调与陀氏的作者立场、作品的思想内容相联系,成为中国接受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时重要的思维模式,日后所形成的围绕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中“作者与主人公关系”问题的争论皆缘此而来。第二,夏文对巴赫金的复调小说做了初步的介绍。夏文确立了巴赫金作为复调小说理论的创始人的地位,指出“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苏联文学批评家米?巴赫金”。接着,介绍了复调的基本概念、复调小说与传统的独白型小说的区别、复调小说中主人公所具有的独立的意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现实主义特色,同时还概述了《陀斯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全书五章的基本内容。但是,夏文的主要目的并非巴赫金及其复调理论,而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地下室手记》。因此,更多的篇幅在于介绍关于《地下室手记》及其评论,巴赫金的复调小说就是作为陀氏研究的“多声部”中的一个声部被介绍进来的,所谓“聚讼百载,莫衷一是”即此真实写照。与前文《窥探心灵奥秘的艺术》一样,虽然夏认为巴赫金的复调小说对于阐释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非常新颖,但多少在介绍中还持着保留态度,或者说一种不太肯定的态度,文中多次使用“似乎”一词透露了这一点。“在所谓复调小说里似乎存在着许多独立的、互不融合的声音和意识,分属于书中不同的人物。每个人物的声音被表现为一种似乎超脱作家意识之外的、自成一体的外在之物。”(着重号为引者所加)在这里,译介者的自我意识嵌入渗透进译介对象的思想观念之中。第三,夏文已经意识到巴赫金复调小说的价值并非仅局限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意识到巴赫金理论的独立性。在对巴赫金复调小说的介绍末尾,夏仲翼发挥道,“巴赫金的这个观点有其独到之处,但也引起很多争论。这是一个十分值得研究的问题,不仅对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即使对一般的文学研究,特别是长篇小说的研究也是一个饶有趣味的题目。” 夏仲翼的这一观点预示了巴赫金及其复调小说理论日后独立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的必然发展。
再来看夏仲翼的翻译。夏译的第一章成为中国早期接受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的重要版本。直到1988年白春仁、顾亚铃的全译本出版,夏译一直在国内介绍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巴赫金的文章中保持了较高的引征率。但是,夏译即使是第一章也并非一章的“全译”。仔细比较,不难发现,夏译对原文删改了两个注释:一个巴赫金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创造一个复调世界,突破基本上属于独白型(单旋律)的已经定型的欧洲小说模式”而做的注释。夏译删掉了“只是到了本书的第四章,我们才涉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体裁传统问题,亦即历史诗学问题” ;一个巴赫金为卢那察尔斯基的论文《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多声部性”》做的注释:“A?B?卢那察尔斯基此文最早刊载在《新世界》杂志1929年第10期上,后曾多次再版。我们的引文据《俄国评论界论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1956年,第403―429页。A?B?卢那察尔斯基的这篇文章,是就拙作(M?M?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列宁格勒,激浪出版社,1929年)第一版问世而写的。” 前一个删节的目的虽然是为了使第一章具有相对完整性,尽量不与其他几章相联系,但在客观上却造成了“历史维度的缺失”,巴赫金所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创造了复调小说,成为前无古人的开创之举,成为与此前一切传统小说相对立的存在物,由于这一删节,国内在接受理解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时一度以为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只是针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的,而对巴赫金在第四章中对复调小说与梅尼普体、狂欢节化关系的历史溯源式探讨并未在意。 。后一个删节删去了巴赫金写作时的复调语境。由于巴赫金的这部书从初版到修订再版历经数十年,因此,这使得巴赫金在进行修订的时候有条件面对评论界对初版《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的意见。在通行的第4版中,既有1版所包含的核心观点,又有后人对之的评述,同时又有巴赫金对后人评述的反驳以及对自己的观点作出的扩充和修正。这就使得巴赫金的《诗学》本身也是“多声部”的,本身也是一种“对话”的产物。这一删节,实际上把巴赫金的《诗学》“独白化”了。尽管夏仲翼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和小说复调结构问题》也提及《诗学》“1929年出版,书于1963年经作者修订改名《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诸问题》再版,目前已出到第四版”,但是1版与4版间的差异以及4版中的这种“多声部”现象直到钱中文与黄梅的争论之后才引起中国的接受者注意 。
1988年,由白春仁、顾亚铃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取代了夏仲翼的译本,成为国内权威的中译本。该译本在并入《巴赫金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中时没有做任何修改,保持了译本的原貌,这在《巴赫金全集》的翻译中是比较少见的。随着《诗学》的译介,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在相当程度上起到了推进中国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的作用。从此,巴赫金和复调小说成为陀氏研究中一座绕不开的山峰。在这一过程中,以夏仲翼为代表的“媒介者”开始让位于越来越多的从事陀氏研究的“接受者”。这些接受者有的阅读夏仲翼的译文,有的同时参阅巴赫金的原著,围绕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巴赫金――复调小说”问题与巴赫金思想展开了对话,各接受者的相互阐发共同推进了中国对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的接受程度。
不过,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对于中国的陀氏研究所起到的作用绝非仅仅是“断裂式”的,在很大程度上(这种程度特别对当事者来说是特别重要的,否则,他们绝对不会允许这种断裂的存在)是一种“延续式”的。也就是说,中国的接受者在接受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时,有意进行了一种理论的嫁接,努力将之纳入当时主流的阐释框架,突出其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意义,从而,在对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的阐释和运用中,出现了多种异质性话语之间的纠缠,“复调”在此也获得了它的“复调性”。这种“延续式接受”主要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其一、努力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特点放到整个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的历史链条中加以理解。从夏仲翼开始,中国的接受者就对巴赫金所概括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现实主义的三个特点特别关注,多方引用 。夏仲翼直接引用了巴赫金的原话并未对此进行任何说明;钱中文在引用了同样的话之后,一反巴赫金对第三点的强调,而把论述的重心转到了前两点。 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使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关系的探讨成为新的热门话题。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同时被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继承现实主义、超越现实主义、具有现代精神而被广泛引征,这也不能不说是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极强的兼容性。继承论者如夏仲翼,认为“这不是主观的文学,这是现实主义的文学” ;超越论者如刘文孝,认为,“他的现实主义的核心是‘寻找人’,把握人的灵魂、人的精神世界,不妨称之为精神世界的现实主义,以别于那些重心在物质世界的现实主义” ,是一种象征性的现实主义。以西方的现代派思想被中国接受之后,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现代主义、现代性关系的探讨进而取代了超越论。现代论者在随后的陀氏研究中逐渐占据显著的地位。如王圣思的《从《〈罪与罚〉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现代性》 ,在此复调小说又被作为陀氏与以托尔斯泰为代表的传统独白小说不同的具有现代性的小说类型来看待了。
其二,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被放到整个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史中加以观照,强调他的继承的一面,而对其具有颠覆性的“发展”的一面,则多加争议。比如说,他们接受了巴赫金所提出来的陀氏作品中的主人公意识的独立性,但拒绝承认主人公与作者处于平等的地位;他们接受了巴赫金关于复调小说艺术特征的技术分析,但不满意巴赫金将之仅仅限定在“诗学”即形式范围之内;他们接受了巴赫金关于“对话”的理论,但不同意巴赫金将这种对话局限于文本之内的分析,更要求“作者与时代与读者的对话”。这种争议正是接受者在将巴赫金置于陀氏研究史中,多种声音并存,异质性话语间展开对话时必然出现的一种现象。值得一提的是,在早期对巴赫金理论的接受中,存在着一处明显的误读。这种误读是从钱中文开始的。钱中文在《“复调小说”及其理论问题――巴赫金的叙述理论之一》中写道,“在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论著中,苏联老一辈的研究家如什克洛夫斯基、格罗斯曼、吉尔波金等人,已经提出了‘复调’、‘多声部’现象,并有所阐发。巴赫金可以说总其大成,并形成了相当完整的‘复调小说’理论。” 何茂正亦在文中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复调’现象,并不是巴赫金首次发现的,苏联老一辈研究家什克洛夫斯基、格罗斯曼、吉尔波金等人也曾提到过这种现象,并作过阐说。巴赫金的贡献在于总其大成,作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并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理论。” 两处论述几乎完全一样,何文明显参考了钱文。但钱文的这种判断是否就正确呢?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研究》20年代写就,60年代修订再版,再版中,对20年代以后关于对复调的评述观点一一再加以评述,这实际上是与“后来者”进行的一种对话,基尔波金的文章发表于1947年,什克洛夫斯基的文章发表于1957年,格罗斯曼的文章更晚,在1959年。由于对巴赫金《诗学》本身的“多声部”现象的忽视或者说将之“独白化”,使得钱中文以及后来的接受者一度以为巴赫金所引述的陀氏研究都在巴赫金提出复调小说之前。中国的接受者并不缺乏俄苏的理论背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一时的疏忽。
第三,巴赫金关于“作者与主人公关系”的看法被整合进马克思主义关于现实主义的理论,使之成为“作者的倾向性”的另一表述。如夏仲翼认为的“作家描述它而尽量不显露出自己的好恶”、何茂正所认为的“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里,表面上作者是完全隐去了……只不过他总是把自己思想的各个侧面巧妙地装进主人公的口中,不直接说出来罢了。……作者的思想、观点和立场是通过人物之口,在巧妙的流露、说明、评价中表现出来的,”并认为“巴赫金后来修改自己的著作时,走到了极端,把主人公的‘自由和独立性’绝对化起来,无限夸大了主人公的主体性。”很显然,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在此几乎成了“作家的倾向性越隐蔽越好”的同义语。在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几乎被解释成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这种有意的误读,虽然对更好地理解巴赫金益处不大,但对于中国恢复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精神、重建中国的现实主义诗学来说则是相当重要的。
从接受的角度来讲,这种“延续性接受”的确是一种误读、一种变形。正如“一切阅读都是一种误读”一样,一切接受都意味着一种变形。在此不是能不能不变形、不误读的问题,而是在承认变形、误读的前提下,分析变形的原因、研究误读的意义。巴赫金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专家是中国接受巴赫金的第一站。由于接受者现实主义期待视野的强大惯性力量的支配,中国的早期接受者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延续性接受”的方式,但是,这种“延续性”必然会受到巴赫金独创性思想的挑战的,必然会因之而促使传统的阐释框架进行修正,甚至改变。早期的接受者尚没有这方面的自觉,因此,在他们的话语中,“异质性话语的纠缠”无时不在,并不时流露出“转变的痛苦”之情。
三、走出“别车杜”:巴赫金之于中国现实主义文论话语的潜在性影响
由于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开宗明义提出了自己的论述角度:“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因此,整个复调小说理论更多地是从艺术思维革命(“复调型”)和艺术形式创新(“复调小说”)方面来谈的。当他的复调小说理论引入中国之后,直接作用于“现实主义诗学”问题是自然而然的。但是,现实主义问题不仅仅是一个“诗学问题”,而且还是一个思想内容的问题、一种世界观、一种批评方法论的问题。特别是中国的现实主义观念长期以来都沿用的是苏联的模式,从别、车、杜(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到列宁、斯大林,从高尔基到卢那察尔斯基,重思想内容轻艺术形式几乎成为现实主义文论的传统。正因为如此,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长期以来(从20年代的俄苏到80年代的中国)所受到的质疑往往最后都落脚到他的基本出发点上:诗学问题。其实,也许当时的接受者没有想到,正是巴赫金这种有意的忽略和绝对化的表述,对中国的现实主义文论话语转型产生了影响。
中国接受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所面临的思想障碍其实是以“别、车、杜”的社会学批评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文论话语方式。这一点,即使是当事人可能也没注意到,他们也往往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到了对庸俗社会学批评所篡改了的“伪现实主义”话语的批判上面,甚至在许多观点上为了反对“伪现实主义”而重提“别、车、杜”,力图借此恢复现实主义的本色。因此,通过陀氏,巴赫金与“别、车、杜”形成一种对话性关系,在各自阐述对陀氏研究的有效性的过程中,两者的意见分歧显露出来。首先,从巴赫金复调小说的研究对象来说,陀氏作为别、车、杜的同时代人,就与他们在思想观念和艺术追求上发生过面对面的交锋。当陀氏最初创作出了《穷人》时,别林斯基曾给予高度的赞
本文来自作者[怜容]投稿,不代表天华号立场,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thwy.com.cn/th/754.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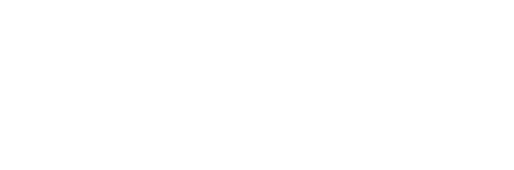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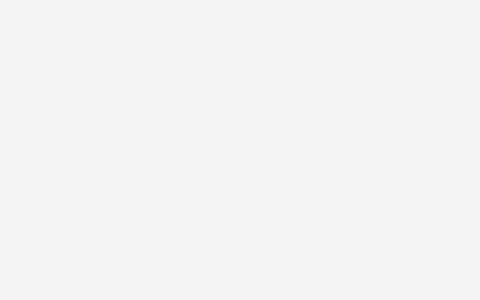
评论列表(4条)
我是天华号的签约作者“怜容”!
希望本篇文章《三国吴国人物》能对你有所帮助!
本站[天华号]内容主要涵盖:生活百科,小常识,生活小窍门,知识分享
本文概览:孙权(182—252)即吴大帝。三国吴国建立者。字仲谋,吴郡富春(今浙江富阳)人,父坚为长沙太守,兄策结交江淮世家,据江东六郡。东汉末,继其兄据有江东,在鲁肃、周瑜辅佐下,治理...